一
1999年,母亲所在的西湖电子琴厂倒闭。
她再也不用在每天天还未亮的清晨骑车穿越大半个城市去上班。最后一笔工资随着工资条发到手上,工厂的卷闸门徐徐关闭,班车上的“西湖”两个字像牛皮癣一样被粗暴地掀掉,那条流水线带走她三年的青春,留给她一台老旧的电子琴,成为我家不足10平方米的客厅里多余的摆设,单薄的声音如同一个噩梦硬生生轧过我的童年。 我后来时常想,如果母亲去的是电视机厂、玩具厂,或者服装厂,是不是我的童年就会多一点快乐呢?至少应该拥有斑斓的雪花屏,成堆成堆的芭比娃娃或者公主裙,而不是雪花般成堆的琴谱。如果没有那台琴,或许我的人生也会完全不一样。
那年我刚读小学,每个周日晚上要去少年宫练琴,几百次放慢脚步走在那条长长的小径上,希望可以就这么一直走到下课。
这是一门无法滥竽充数的艺术。琴弹得最好的女生上课也都是由父母陪伴,赞扬声于她而言不过是快乐被冲淡后的沉默,这种司空见惯的强迫,在我记忆中毫发毕现。老师坐在我身旁,总是皱着眉听我弹完死记硬背的曲子,指着她对我说:“她闭着眼睛都不会是你这样的水平。”哄笑声中我感觉到肾上腺素在飙升,脆弱的自尊心碎了一地。 他们乐感极佳,听一遍曲子便能在指尖流淌出悦耳的琴声,在还未学会汉字之前便已熟悉如何跟五线谱打交道。我学了很久,依然看不懂五根黑色线条上蝌蚪般浮动的音符,沉默如谜的排列组合让我的神经隐隐作痛。母亲只好对着谱子弹曲子,弹会了再教我弹,把我推到教课的老师面前,以一种近乎作弊的方式,让我像是自己琢磨出来一样弹给老师听。 我和住在楼上学声乐的伊雯一样,对音乐产生了一种源自本能的抵抗,痛恨它打劫了我们过多的时间。我们疯狂吃辣,大声吼叫,把手指骨节掰得咔嚓作响,试图摧毁我们与音乐最后的一丝关联。伊雯常常为了不去上课把自己弄得鼻青脸肿,最严重的一次,头撞在玻璃上鲜血直流,父母吓得一路哆嗦着把她送去医院。
“为什么我必须做不喜欢的事情,你别以为我不敢像伊雯那样……”我感到枯燥、乏闷,我是在浪费时间。我想像那些放课后冲回家看《花仙子》的女孩一样,正正经经享受我应有的自由与快乐。我妈听我说完后,抽出衣架狠狠敲在我背上,把我的呜咽封锁在阳台外面,只丢下一句“不练完不许吃饭”。
她不在的某个日子,我看着那台带给我诸多痛苦的琴,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怒意,狠狠把它摔在地上,拗断它的支架,用剪刀剪碎变压适配器,下定决心要和它一刀两断。
我忘不了母亲惊愕的眼神,以及恢复镇定之后劈头盖脸的巴掌,在我背上留下一道道淡红色的掌印。后来她去旧货市场淘了很久,终于给我找齐当时已经停产的所有配件。她目光锐利,口气生硬,脸色难看,“你得挨过去,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对自己不负责。”
二
当我拿到那张电子琴十级证书时,我以为母亲对我的桎梏结束了,内心破土而出的是一种解脱感。
我升入一所寄宿制的高中,学琴而导致的文化课短板像黑洞一样很难填满,当我捧着不及格的卷子哭着找母亲签名时,她拒绝了。班主任在全班点名批评我是无法上交签名的差生。我回到家摔碎了花瓶冲她发脾气,埋怨她让我出糗,母亲平淡地回应:“你不想丢脸的话,就好好努力。再考这么差,不如退学吧。”
那时MP3刚刚开始普及,在空荡荡的卧室把耳机里的声音放到最响,手边堆满厚厚的习题册,不听流行歌曲,倒是以前反复练弹的曲子让我心安,《胡桃夹子》轻快悠扬,《拉库卡拉查》柔美抒情,《匈牙利舞曲》激昂热烈,旋律像完美的情人,激发着我的灵感。
母亲发现时总是粗暴地扯掉耳机,“不许在做作业的时候听这些!考试时会给你放音乐吗?”她勒令我将里面的音乐删光,替换成美国之音,让我在校车上听,在晨跑的时候听,在睡觉前听。这种见缝插针的方式像一层保鲜膜把我勒得难以呼吸。我的成绩慢慢回温,却越来越抗拒回家,总是坐在公园长凳上直到入夜后空气转凉,闻着潮湿的泥土气味慢悠悠地踱步回家,避免与她在同一个空间里单独相处,把晚归的原因解释为留在学校艺术团练琴。
她偷看我的手机试图找到我晚归的原因,我质问她为何热衷于偷窥隐私,是不是愿意也共享一下她不曾离身的笔记本。母亲看了我一眼,那目光中含有太多失望的情绪。她终于败下阵来,叹了口气把本子交到我手里。这本破旧的笔记本她用了很久,纸张松散,字迹潦草,沾着柴米油盐的生活气息,随便一翻全是关于家庭开支和我成绩变化的记录。她坚强而敏感,一定看穿了我编织的拙劣谎言。我学会独自消解心事和秘密,她也从不跟我分享飞涨的物价和生活的艰辛。
其实我知道母亲偷偷找过很多工作都碰壁了。那段时间家里订的报纸,边边角角的招聘信息都被她做上记号。她瞒着我报名去当学校宿管,在报名表上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姓名,年龄,籍贯,当然最终还是落选了。
40岁仍旧经历生活的潦倒是件残酷的事情,相比之下年轻时所受的苦难都太过轻盈。所以她希望我能尽早成为经得住打磨的人,拥有不会流血的心,获得不失控的人生,不用像个打了败仗的将军,无条件接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条约。
三
当我终于考上我心仪的大学和专业时,我才忽然发现当初怨恨的其实是自己的无能和懦弱,恨自己永远无法企及母亲的标准。
我没有想到弹琴居然会成为我撕不掉的一个标签,在陌生环境中的自我介绍过后,总能成为别人印象深刻的那一个。也是因为这门技艺,大学时可以去咖啡馆兼职弹琴赚生活费,给学校微电影配乐获得额外的学分。
大四去外地实习,我和学姐在一家设计公司跟着导师做项目。我们学会了抽烟,每一个跟甲方纠缠的夜晚我们都能抽完一盒万宝路,淡淡的薄荷味混杂烟味在漆黑的天台上明明灭灭,如同一只只迷失在深海的浮标,烟蒂把垃圾桶上那个小小的烟缸塞得像个刺猬似的,焦虑和迷惑的负面情绪蚕食着每个人的意志。
生活泥沙俱下,像一个无底洞,零零散散支配着我们的热情和体力。实习工资扣除房租后所剩无几,我却格外珍惜这短暂的自由。母亲在我的生命里徐徐退场,安分守己地做一个旁观者,她不再过问我生活的细节。偶尔打电话过来,只进行简单的交流,最近过得好吗?什么时候回家?
实习生陆陆续续离职,但那是我活得最饱满的一段时间。白天用来跟业务方斡旋细节,晚上就开始对着设计的图纸一遍一遍修改、描摹。看着窗外的城市夜幕降临,恍惚之中我想起年幼时反复练琴的场景,练到不能弹错一个音符,练到整首曲子的情感和力量保持一致,练到每一个拍子不早一分,也不晚一分。原来在这些漫长的时光之中,它们早已潜移默化成了我性格的一部分,让我对任何苛刻的要求安之若素。
“我觉得喘不过气。”学姐在几个月后因为不堪业务方的压力,抄袭设计而被开除。公司墙壁上的摄像头,24小时对准我们的办公桌,每个人的电脑里都被安装上监控软件,时刻关注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。这家公司以前的设计方案被泄露过,不得不用这样的手段来防范。
在酒杯里漂浮的泡沫上,形形色色的业务方偶尔开一些低俗的玩笑,饶有兴致地等待我们巧妙化解这种种危机。导师则把我们当成免费的劳动力,开会时蛊惑我们为了梦想,为了免费的丰盛夜宵,为了报销打车费,欢乐地加班吧。 而这些毫无尊严的时刻,我早就在阴郁的少女时代就有所体会,它们在我身上形成一种抗体,让我拥有充分自我治愈的能力。
学姐后来被查出患上轻微的抑郁症,需要定期去找心理医生复诊,她离开的那天我送她去车站,她对我说:“你是我见过的最独立的女孩,真的很羡慕你,有这样一个妈妈。”她在温和甜美的家庭氛围里长大,父母未曾对她大声说过一句话,生活的考验来得有些迟钝。
我终于理解,母亲带我预习了成人世界里的潜规则,那些年我一直在尝试把做不好的事情干漂亮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天赋异禀,没有显赫家世。世界是个巨型斗兽场,在把选择权握到自己手里之前,至少可以做好最坏的打算,以失败者的眼光来解读每一个成功的侥幸,并且永不停歇地战斗下去。
实习期结束,晚点的火车在晃晃荡荡摇摆了几个小时之后,终于穿梭过呼啸的风雪抵达我心心念念的家人身边。
四
《爆裂鼓手》里有一幕打动了很多人:因为过度严厉被开除的教练,落魄地坐在逼仄的酒吧里对学员坦白:“我不是去那儿指挥的,我是去逼他们突破自己的极限,我认为那是绝对不可或缺的。”这个被揭露的谜底让我瞬间红了眼眶。
时间显山露水,那一刻我终于承认,生命里很多考验都是为我们这些庸人量身定制的,迟早会有一瞬,我们会摆脱那些必经的错落疼痛,在现实的尘土飞扬之中,感受到自己内心深处温煦的音乐,与这座城市轻轻共振,宛如流星划过寒夜,如此明亮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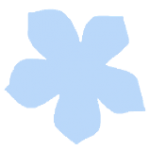
● 作者:若怀特
● 摘抄于《女报·时尚》2016年3月






